8月8日晚,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产生7.0级地震。到9日22时,已构成19人逝世、受伤343人。
咱们没有忘掉,9年前,四川汶川县产生8.0级地震。也不曾忘掉,4年前,四川雅安芦山县产生7.0级地震。
四川,自古称“天府之国”,却也是一个震情频频的当地。该省境内散布数条地震带,导致大地震频发。
在历史上,四川相同常常遭受“地动山摇”。被《明实录》和《明史》记载下来的明代地震灾祸共1159次,其间四川区域的地震灾祸次数为98次,占到总数的7.38%。
现在,大地震产生后,从政府到民间的灾情应对现已颇有经历。那么,在古代,官方和民间是怎么样做出应对地震灾祸的呢?皇帝/官员会观察慰劳灾区吗?也会有灾后重建吗?
————————————————————————————————————
古代我国已根本建立起一套相对体系的地震灾情应对机制,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政府救助准则更为完善。其间的许多做法,咱们现在看来仍会感觉非常了解。
报灾准则历代极为注重。比方明太祖朱元璋清晰,“中书省其行全国遇有灾变即以实上闻”。
明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536年3月19日),四川行都司建昌卫(今四川省西昌区域)产生特大地震。地震产生之后,其时的四川巡抚都御使潘鉴就收到了四川行都佥事、都指挥佥事曹元的陈述,并依据陈述内容做《巡抚都御使潘鉴亟处严峻灾患疏》一文上书中心,据实陈述灾区的状况,以期中心据此赶快作出正确合理的决议计划。
中心在接到当地灾情陈述之后,一般会派员核实,以便采纳下一步办法。朱元璋从前下诏“从实踏勘实灾,租税即与蠲免”。
仍是以上述嘉靖十五年四川行都司建昌卫特大地震为例,中心在在收到灾情陈述之后当即对灾区的状况做核实,进而对哀鸿进行抚恤。
因为触及地震灾情救助,陈述及核实灾情越具体越好,这就构成了灾情计算。明代地震丢失的计算内容有人口、家畜、房子、城墙等。
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辛酉元旦,陕西产生地震。依据官方计算,此次地震使陕西朝邑县“军民房子震摇坍毁共五千四百八十五间,压死巨细男女一百七十名口,压伤九十四名口,压死头畜三百九十一头只”。

历史上并无皇帝观察慰劳地震灾区的记载。但能确认的是,历代中心都会派出使者奔赴灾区。
汉代在地震之后,常派使者赴灾区了解灾情、民意,一起,以使者“循行全国”来安靖民意。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因为地震,中心差遣光禄大夫等12人,循行全国,“存问耆老鳏寡孤独疲乏渎职之民,延登贤俊,招贤侧陋,因览习俗之化”。这说明循行使者的使命是慰劳大众、招纳贤才、了解习俗民意,但对灾祸救援并无本质含义。
隋朝今后,奔赴灾区的使者除了慰劳哀鸿,则兼具赈灾功能。明代,除了当地官员暂时进行赈济以外,中心会按照当地的要求第一时间派出官员到灾区进行赈济。
针对哀鸿,首要发放什物,包含粮食、衣物、酒肉等。明代地震赈济分为国家与当地两方面,其间,国家方面动用国库帑金、京通仓粮、盐税、地丁银等帮助哀鸿,而当地官府除使用常平仓、准备仓、社仓的平粜进行赈济外,还发动当地绅士、名人、大商人捐助粮食与银两,使用社会的力气来救助哀鸿。
因地震灾祸的忽然产生,有些当地官员为了救助哀鸿乃至会将军粮发放到哀鸿手中。比方明嘉靖十五年四川行都司建昌卫那次特大地震,钦差巡抚都御史潘鉴“预付军粮,优恤被灾人户”。
地震极易构成人口伤亡,对地震中死难者进行安葬、对受伤者供给必定的医药费成为救灾作业之一。
首要是革除田租赋役。在地震灾祸这样的大灾面前,哀鸿的根本生计尚不可以保证,其本身所承当的税收就更是无法准时实现上交,故中心的免税办法往往都是无法之举。
公元前70年震后,汉宣帝诏定“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公元前48年、前47年,接连地震,汉元帝也接连两年下诏:“令郡国被灾祸甚者毋租借赋”,“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无租借赋”。
大地震往后,往往构成权利真空期,骚动在所难免。维稳也就成为一项重要作业。
嘉靖年间,直隶安州产生地震,成果引起了大变,“州人乘乱抢杀,目无官法,上司闻风畏避,莫知所出”。这时,当地一名退休官员杨守礼挺身而出,安排家丁维稳,将带头作乱者斩首,悬其头于四城门,很快就使社会次序趋于稳定。
嘉靖十五年,四川行都司产生特大地震。监狱在地震当中被损毁,很多监犯外逃。为了敏捷安慰大众,保护次序,其时的四川巡抚都御使潘鉴当即作出决断,指令罪犯自首,建功者给予弛刑。总算保护了灾区的社会次序。
灾异催生流言。在明代,地震流言中最闻名的是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古城陆沉”说。该传说首要意思是西昌区域的建昌卫会因地震灾祸而整个城池淹没下去,构成一个大型堰塞湖。流言导致当地居民惶惶不可终日,更有甚者争相外逃,差点激起民变。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云南嵩明产生8.0级特大地震。在地震灾祸的勘测过程中,各州县官员是否尽职尽责,灾情上报是否及时,云南督抚对此分外的注重。知县赵发却在震灾的勘测过程中成心拖延时间,未能协同其他官员查明灾情,因而遭到督抚问责和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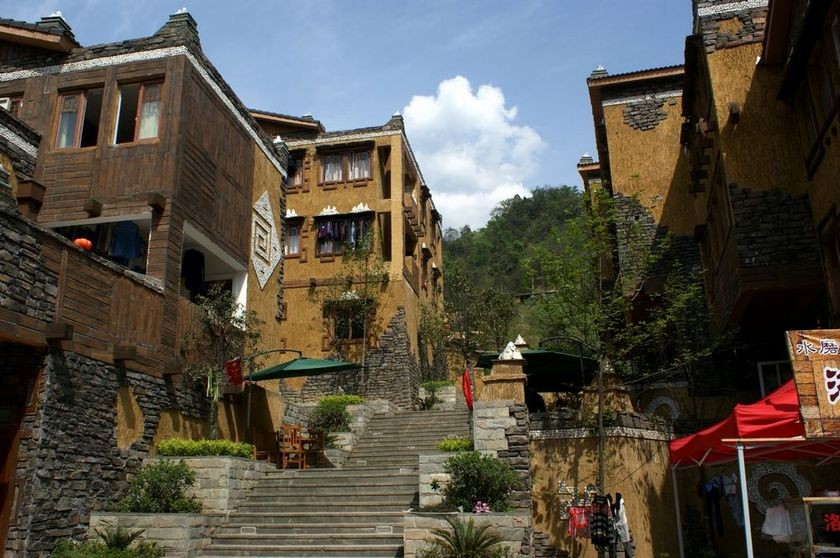
古代的灾后重建的力度跟地震损坏力成正比。地震对当地的损坏越严峻,重建力度就越大,也越困难。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云南嵩明8.0级特大地震致使昆明等十州县的城垣、衙署坍毁甚多。府城昆明墙垣和鼓楼一半以上被炸毁。云贵总督伊里布就任后,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重修。澄江府城在地震中崩塌严峻,震后花了12年才补葺结束。处于地震中心的嵩明州城垣倾圮过半,衙署损坏严峻,州城的建筑一直到咸丰九年(1859年)才得以完结,耗时长达26年。
————————————————————————————————————
现在,咱们都会用科学来解说地震,以为自然灾祸便是自然灾祸,与政治无关。但在古代我国,统治者信仰天人感应,以为灾异是天谴,需要与“天”、“神”等交流,以求免除天谴。
也便是说,他们常常把地震等自然灾祸政治化。因而,大地震产生后,最高统治者一般会采纳许多现在看来非常迷信或奇葩的办法。

地震产生后,西汉帝王会从“灾异谴告”的视点去反省自己施政的得失,下诏自责,以求获得上天体谅。比方,公元前70年地震后,汉宣帝下诏自责。
一起,汉宣帝还穿素服、避正殿,显示出对灾异的惶惑之情,并改元“地节”。历史上以“地”字最初的年号,除王莽时期曾时间短用过“地皇”之外,“地节”是仅有的一例,表达了期望土地安稳平定的祈愿。
天灾面前,皇帝还要广泛寻求谏言,以到达完全批改“德行”的意图。西汉时期屡次地震之后,都有求谏言的诏书,要求公卿有司“思朕之过”,“明对缺咎”,表现出敞开、谦虚的纳谏情绪。
天人感应论以为狱中有冤气,会导致天降责罚。因而,大赦全国是缓解社会矛盾的手法之一,也是应对地震、安靖社会次序的重要办法。公元前131年、前70年、前47年震后都有“大赦全国”的行动。
地震之后的救灾行动中,常有“举贤能”的诏书。这些所谓“贤能”并非专业的救灾、禳灾人才,大多是契合“德行”要求的人,如公元前70年要求“举贤能方正”、前47年“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等。
地震后厉行节约。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因地震规则郡国中止建筑楼堂馆所。明永乐元年(1403年),北京、山西、宁夏诸地皆地震,朱棣决议中止大兴土木,赶快使国家安居乐业。
经过一系列迷信活动求得心安。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产生大旱与地震,明宪宗“遣右副都御史赵文博祭祷中岳”。正德四年(1509年),北京产生地震,明武宗谕令称:“朕心惊惕,尔文武百官同加修省,致斋三日,祭告六合宗庙社稷山川。”
潘明娟:《古代震灾及政府应对办法——以西汉关中区域为例》,载《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年第1期
聂选华:《危机与应对: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祸研讨》,载《昆明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